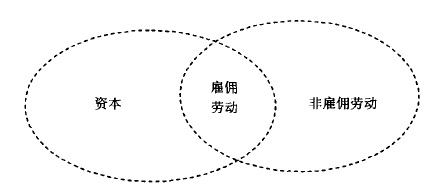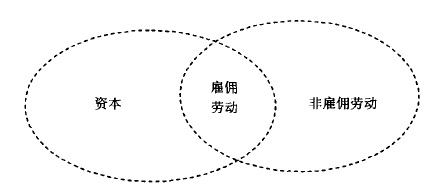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1992)
第8章 雇佣劳动的片面性
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潜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1]
——卡尔·马克思 |
8.1 雇佣劳动的抽象概念
我们理论化的并称之为雇佣劳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显然,在资本主义中它是资本的对立面。雇佣劳动是资本增长的必要媒介。资本的再生产需要雇佣劳动整体的再生产和大量的人类生产工具进入到为资本创造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中。因此,雇佣劳动是资本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们同时注意到,雇佣劳动不仅仅指这些。雇佣劳动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加入到与资本的社会关系中来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察,雇佣劳动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获取必要使用价值的手段。简言之,雇佣劳动不仅仅是手段;它是自身的运动方式。从这个方面说,资本是雇佣劳动的媒介,是雇佣劳动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139〕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资本主义整体的全面理解要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具有两面性,《资本论》只从资本的角度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展开,因此它是片面的。只要考察一下就扩大再生产(包括资本家的扩大再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扩大再生产)展开的斗争,即两个“应然”之间的斗争,我们就能把握资本主义特殊运动的规律。这第二个方面的发展对于正确理解不同阶段的相互关系和资本主义有机体系的内部区别是必要的。
相应地,我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整体概念是一个既包括K—WL—K又包括WL—K—WL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资本与雇佣劳动构成一个整体[如图5.1(I)所示],该整体的特征在于双方互相敌对并展开双向的阶级斗争,从而推动资本主义沿着它的特殊轨道前进。
然而,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却没有在图表中表现出来。如果说这个概念照理应该代表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整体,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提出的很多问题以及我们在第2章指出的问题依然是实质性的。这个重新构建的整体所推测的所有假设都是结果,所有的结果也都是假设,对此我们仍然可以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资本对劳动者持续实行霸权主义;而且缺乏关于下列斗争的理论(与相关实践):即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女性反对父权的斗争,就生活质量和文化身份而展开的斗争——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理论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
尽管我们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把劳动者看作是“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2]),然而我们在此提出的整体概念似乎依然只考察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直接阶级斗争。以现实具体的整体标准来看,资本主义整体理论也是“有缺陷的”。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提出的雇佣劳动概念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只是允许我们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考察雇佣工人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概念是“合理的抽象”。[3]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与之相似的动物——雇佣劳动仅仅存在于有进入到这种关系的有生命的个体之中。因此,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可以成为雇佣工人的人。〔140〕
但是,这样的人类个体不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迄今“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4]仅仅被看作是特殊经济关系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界定是明确的:“这里所涉及的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5][i]因此,尽管我们对雇佣工人的论述超越了《资本论》,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脱离它;我们认为雇佣工人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类个体,他们只是雇佣工人而已。从这个方面我们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这真的是个问题吗?马克思早年确实认为如此。他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6]这不是偶然的评论。很显然,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他们是资本家或劳动者这样的情况看作是个体存在的原因(或充分的条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但是,既然他们仅仅存在于与资本的这种特殊关系中,我们该如何对这种真实、确定的劳动者作出评价呢?正如黑格尔所说,任何确定的个体都有其存在的多方面性质(Grounds):
“事物是由多方决定因素所凝结的具体体现,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是具有同样的生命力和持续性的。因此,每一个因素和其他的因素一样都作为性质(Ground)而被决定,即都作为必要因素而被决定,其他的因素也是其存在的结果。”(Hegel,1961:Ⅱ,p.92)
〔141〕总之,任何特殊的限定都可能被看作是其存在的原因,而其他因素则被认为不那么重要。“例如,一个政府官员会有做官的某种天赋,会与其他个体之间存在某些关系,会有这样那样的熟人,会有特殊的性格;他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自己,等等。他的每一种特征都可能是或被看作是,他拥有这个职位的原因。”
事实上,对于政府官员这个职位,这些特征无———不是重要的,“因为正是由于这些性格特质,他才成为称之为他的确定的个人”(黑格尔,1961:Ⅱ,p.93)。不过,在确定特殊性质(grounds)时存在一个固有的问题,即:
“在实质上,某性质(Ground)与其他性质是具有同样效力的,但它并不能将事物的整体包含其中,因此,它只是一个片面性的性质(Ground),同样,在这个性质群中的其他部分都是与之相同的。没有一个性质能够穷尽事物的全部,而事物则是由这些性质相互联结构成的,并将它们包含在内。不存在充分的性质,这就是定义(Notion)。”(黑格尔,196l:Ⅱ,p.94)
马克思早年批评政治经济学忽略了个体存在的多种决定因素,而只把资本家或劳动者身份看作其原因,从而明确说明,只有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所有特殊原因的相互关系,才能找到其存在的充足基础。从这个方面看,仅仅把人类个体看作是雇佣工人显然是片面的。在资本的政治经济看来,无产者“只作为工人”,“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7]
那么,是否正如E.P.托马斯(E.P.Thompson,1978:pp.60~63)所说,马克思晚年确实忘记了这些因素而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陷阱中”呢?他忘了劳动者也是人类个体了吗?有证据证明马克思持续强调人类个体的存在有多种决定因素,要将这种结论与这些证据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到处可见诸如社会人类需求具有多面性这样的论述,不仅如此,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也曾明确提出这样的评论,即:“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总之,在马克思(无论早期还是晚期)看来,在把人类个体作为考察对象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8]
〔142〕因此,不是说马克思忘了劳动者也是人类个体,而是说他在对必需品标准进行论述的时候确实忘了这一点——他在《资本论》中假定考察的个体仅仅是特殊经济关系的承载者,仅仅是经济逻辑的化身。[ii]然而,这不表示马克思确信这种假设是充分的,而是他认为必需品标准实际上是固定的。就像他随后向恩格斯提到的那样,“仅仅通过这个程序就可以对一种关系进行论述,而不需要论述其他”。
当然,问题在于马克思本人后来没有排除这种假设而将人类个体作为对象进行考察。只有当我们超越了《资本论》并对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的著作的主题提出质疑时,我们才能探究那些对劳动者的确定发挥作用的“所有的人类关系和相互作用,无论这些关系和作用是否会出现或者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我们在对雇佣劳动的论述中一直暗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不仅仅是雇佣工人。这点从我们对生产的“第二阶段”——超越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雇佣工人的生产中可以明确看出。此外,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也看出了这一点:从劳动者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使用价值进行的论述;对自然也是劳动者的财富之源的假定;包括为促进人类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在内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
总之,雇佣劳动的真正概念不仅包括那些必要的雇佣劳动而且包括那些尚未耗尽仍然包含于同样的雇佣劳动之中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内部是有区分的,分为作为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和作为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因此,图8.1对资本主义整体的描述是不恰当的,确切地说,资本主义整体的关系应该如图8.2描述的那样,表现为两个部分的相互重叠。这种表示与前文对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论述是一致的。〔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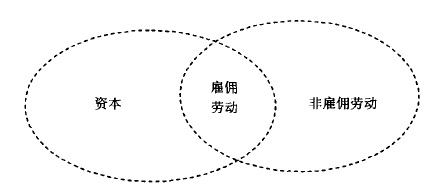
图8.1 整体资本主义(Ⅱ)
8.2 作为非雇佣工人的雇佣工人
对于马克思理论框架中雇佣工人的另外一部分(和劳动者的决定因素),我们该如何评价呢?首先,让我们回到作为劳动过程的工人生产概念上来(如第4章所述)。和其他人类活动的产品一样,生产出来的工人的具体特征不仅取决于生产投入的特征,还取决于将这些投入转化为最终生产成果的生产过程的特征。
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仅通过消费食物来实现,还通过“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9]这样,劳动产品的性质就会随着生产过程的改变而改变。“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10]简言之,就像在第7章提到的那样,生产出来的人类个体的质量同被消费的投入的具体特征不是相互独立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11]
当然,这种投入,即劳动者在自身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使用价值,是与“各种不同的需求”相一致的。它们不仅包括体力再生产必需的物质性投入,还包括“更高的文化需求”所要求的各种投入——如报纸的发行,会议的参与,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品味的提高等;不仅包括具有使用价值的有形物质(来源于“胃或各种想象”的需求),还包括来自于自然界的“新鲜空气和……阳光”等。[12]
〔144〕但是,这些使用价值是如何获得的呢?显然,对雇佣工人来说,可以用出卖劳动力得到的货币购买消费品,从而获得一部分使用价值;另外一部分使用价值的获得则得益于劳动者在社会中的成员资格——就好像罗马市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等等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13]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现代社会”是存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14][iii]劳动者需要的其他使用价值(如新鲜空气和阳光)则可以看作是自然力为人类提供的“免费服务”。
但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些供工人消费的使用价值在工人自身的生产过程中都是原始存在的。其实它们不是,劳动者需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以使其适合自己的需要。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这些活动;但是,他强调这些行动的采取取决于资本劳动的前期实现。他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生产了可以支付肉价的工资,才能给自己煮肉;他只有生产了家具、房租、靴子的价值,才能把自己的家具和住房收拾干净,把自己的靴子擦干净”。[15]马克思一直把劳动者采取的这些行动称为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非生产性的活动”(当然,这是从资本的角度说的)。
马克思将“消费物品时绝对必要的”行为称为“消费费用”。[16]②他指出,每个劳动者都要执行一定数量的、非生产性的、部分地计人消费成本的功能。“真正的生产工人必须自己负担这些消费费用,自己替自己完成非生产性劳动。”[17]③当他们为自己进行这些活动时,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会有所降低。马克思指出,在家族劳动背景下的“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要低于“购买现成商品”背景下的成本。相反,“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18]④
所有这些都暗示资本范围之外存在的生产过程不止一种——不仅包括人类个体自身的生产过程,还包括为人类生产充当原料的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当然,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后一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当自由劳动者亲自进行那些“绝对需要的”活动时,他们〔145〕既是自身劳动力的拥有者,也是作为生产手段的使用价值的拥有者,因此他们也是劳动果实的拥有者。当然,这些劳动既是“绝对需要的”劳动,也是劳资关系之外的私人劳动。因此,这种劳动(马克思承认其存在并将之称为“非生产性的”)在资本看来是“无形的”,因为他不必对此进行支付。[iv]另一方面,由于假定这种劳动占有了资本生产的产品,从这个程度上说,“如果他们不先进行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是决不能使他们重新进行同样的非生产劳动的”。[19]
但是,特殊情况下我们会把单个劳动者看作是孤立的,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提出的那样,个人需要彼此联系,“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20]那么,这些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通过很多可能发生的关系都可以获得雇佣工人的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21]两个雇佣工人之间发生的等价交换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劳动力的拥有者都不断地进行这种必要的私人劳动(这种劳动对资本来说仍然是非生产性的),但是二者之间的私人劳动也存在分工。
另一种可能的劳动分工是这样的:“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22]马克思指出厨师、女仆、医生和私人教师的付费活动都是“非生产劳动”,而相当多的服务活动都属于“消费费用”。同时,不仅这些“非生产劳动”的持续进行需要雇佣劳动的持续供应,而且“消费物品时绝对必要的”劳动作为劳动分工的结果也不会轻易改变其特征;它们仍然是私人的,只有在雇佣劳动超越了资本家的消费成本以后才会被看作是“社会的”。
不过,(出于某种逐渐明显的原因)让我们集中考察一种可〔146〕能会发生“非生产性”劳动的特殊关系,即劳动者拥有奴隶所有权的情形。由于拥有奴隶的所有权,雇佣工人可能通过生产和交换之外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剥削来实现——可以简单地看作是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在奴隶关系中,受控的生产者“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23]此时,劳动力不“属于”这个受控的生产者,对劳动力的消耗(和劳动果实的享有)进行安排是奴隶主的权力。奴隶生产出来的所有使用价值和他们自己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但是,奴隶主必须把这些使用价值的一部分分配给他的“劳动机器”才能保持他们作为奴隶主的天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经济强制,不如说是“直接的强制”在维持着奴隶的地位。奴隶在恐惧之下进行工作——尽管“不是为了自身生存而劳动,这种生存并不属于他,然而生存是有保障的”。[24]
剥削意味着奴隶“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25]这表示奴隶主通过接收剩余产品和/或“自由时间”(减少“进行消费的绝对必要劳动”)而受益。自由时间——多么具有批判性啊!这个时间不仅是人的能量进行恢复的时间,而且是人的能力进行提高的时间。马克思指出,在历史上,不劳动的人可以自由处置的自由时间:
“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
[26]
总之,“一方的人的能力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简单来说,“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过度劳动时间。”
[27]
由于奴隶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和自由时间都上交给了奴隶主,奴隶的劳动对奴隶主来说显然是生产性的;在这个程度上说,奴隶既生产奴隶也生产奴隶主——也就是说,这促成了奴隶关系的再生产。然而,对资本来说,奴隶的劳动仍然是私人的、非生产性的;只有雇佣劳动成功地获得货币——购买商品满足奴隶的必要生活需求——以后,他们的劳动才转化为“社会”劳动。同样,奴隶主通过雇佣劳动满足这些货币需求的能力也成为维持奴隶关系的条件。但是,劳动力价值不包括奴隶必需的供应品的价值,因为资本希望雇佣劳动拥有奴隶!这又是一个与前面提到的片面的劳动力价值概念相一致的谬论。更恰当地说,当工人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必需产品的供应以后,劳动力的价值包括这些产品的价值。
尽管对这种特殊关系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固有规律进行研究是可能的,但是却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对雇佣工人的生产进行讨论的背景下,为什么对奴隶所有权的恐惧甚至会有所提高呢?因为这恰恰是马克思当时对家庭关系进行描述的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提到了“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指出“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后者拥有“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的权力。[29]同样,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强调共产主义纲领将废除“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和“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30]
马克思的《资本论》显然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他指出:“在〔148〕这种形式的私有制中,至少总是包含着纯粹被家长驱使和剥削的家庭成员的奴隶制”。[31]恩格斯随后也评论说:“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上”。[32]
在把家庭内部关系定义为一种奴隶制时,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33]以及“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34](包括“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的活动)[35]都产生于生产者在一种奴隶关系下被剥削的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否认这不是马克思的主张呢?
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观点。南茜·弗尔博(Nancy Folbre)指出,由于一直“不愿意对再生产领域内的剥削状况进行考察”,结果这种剥削的“存在性在关于家庭劳动的争论中被大量地否定了”(Folbre,1986:p.326);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奴隶关系被看作是“比喻性的而非科学的”——事实上,这会引起“危险的比喻”(Vogel,1983:p.61,p.130)。然而,这种主张不仅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断章取义,而且忽略了马克思观点的一致性。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种以家长权(“父权”)为特征的“旧家庭制度”[36]随着贫困化的提高——这种提高是由实际工资的下降或社会需求的增长造成的——而发生的变化。一种选择是加强家族内的剥削,即增加妻子和孩子的劳动量。我们知道,家庭内劳动消费的提高会导致外部花费需求的减少。关于对孩子的剥削,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37]〔149〕
然而,当工资太低以致无法满足需求时,还会发生另一种可能——直接延长劳动时间(当增加后的家庭劳动也无法满足需求时就可能发生)。当工资不足时单个劳动者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从而使劳动供应“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38]),我们发现当“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39]时候,劳动者家庭的劳动供应也是如此。当需要更多的货币时,他们会通过“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40]从而向资本提供更多的劳动。
在本质上,这种发展状况并没有改变“家长”及其剥削对象之间的关系——古代的奴隶主把奴隶出售以后不再是该奴隶的主人。家庭内的奴隶变成了为满足更多附加的货币需求而赚钱的奴隶。这确实是马克思描述的发展状况。他指出,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41]男性雇佣劳动不仅仅出卖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42][v]
当然,马克思的确主张这种特殊的过程,其中资本“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之外,在社会的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43]追求短期利益的事物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根本不矛盾。[vi]马克思为什么要把这种发展看作是家庭内部社会关系潜在改变的基础呢?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劳动力的出卖者是“真正的人”,劳动力是他们的财产。因此,随着女性逐步进入雇佣劳动过程,“古老的家庭关系”将会宣告结束:
“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44]
那么,这种奴隶关系的精确设计到底是多么重要呢?这种说法会让很多男女平等主义者感觉不舒服,当然马克思当时描述的并不是把人当作财产(如对人进行买卖)的所有情形。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著作的学习者,应该明白马克思描述的是古代社会的奴隶制(而不是新社会的),这种奴隶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包括:由于奴隶可能的选择不被接受而自愿进入这种状态的个体的特征)。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而在于这种情形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剥削。马克思描述的这种情形与南茜·弗尔博(Nancy Folbre)的论述是一致的。南茜·弗尔博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外,雇佣劳动同时处于“生产的家长制模式”(patriarchal mode of production)中,她把这种情形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种关系形成了男人对女人和/或儿童的剥削”。(Folbre,1986:p.330)
由于我们在此想要表明的是马克思对劳动者决定因素的考察状况,因此我们不必继续展开。无论妇女和儿童加入雇佣劳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男性雇佣劳动当时都处于两种阶级关系中,即作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发生的关系,以及作为奴隶主与奴隶发生的关系,这是很明显的。他根本不是抽象的雇佣工人,而是家长制的雇佣工人!
同样,妇女和儿童成为雇佣工人以后,他们也会处于两种阶级关系中。简言之,我们所说的雇佣工人其实是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们唯一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我们以资本为主题,我们就可以只考察这些人类个体作为雇佣工人的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以雇佣劳动为主题,考察这些人类个体的其他方面就是完全必要的。
通过对家长制关系中的男性和女性雇佣工人进行描述,我〔151〕们发现劳动者拥有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等级需求。对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来说,为提高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家长制的再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的工资提高就可以满足他在家庭内更高的劳动消费,从而可以让他的妻子(和孩子)提供更多的劳动。(“家庭工资”是他所处的这两种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对女性雇佣工人来说,为提高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这种关系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关系中,男性控制着家庭内的生产方式,剥削着妇女和儿童;事实上,这也是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时间而进行的斗争,是她们为了自己的发展立足于自身的需要展开的。
当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雇佣工人之间存在利益分歧。如果把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作为主题,我们在第5章就雇佣工人的斗争展开的论述就会稍有不同。如其他情况不变时,每个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即“家长”)在资本的影响下,都会让家庭内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雇佣劳动中来,不会考虑家庭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然而,当所有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都这么做时,竞争会加剧(工资会降低),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整体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通过自愿签署协议向资本出卖妻子和孩子的能力就会受到制约(通过“占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这是处于家长地位的雇佣工人整体开展政治运动的结果。[vii]
但是,家长制的含义不止于此。在这种家长制关系(或奴隶关系)中,男人和女人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我们注意到,后来“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然而,所生产的人类个体的特征无法摆脱他们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
“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46]
“这里由于在利用所购买的使用价值上的特殊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就使得这种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即使不是在经济形式上——发生形态变化,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
[47]
因此,从一出生开始,男性和女性的自我生产就不仅消费由劳动的性别分工创造的使用价值,还消费决定这种分工的家长制关系。那么,这个生产过程就包含着不同人的生产,不同人格的生产,以及与支配和养育相关的不同种类的生产。正如山蒂·哈丁(Sandra Harding)所强调的,“人的成长是极大地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在从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婴儿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的过程中,人们经历着转化和自我转化。”(Harding,1981:p.147)[viii]
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是由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论者提出的,他们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因此,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局限性进行评论并无不当。尽管马克思指出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家庭内部存在的关系是奴隶制的,但他却没有考察这种阶级关系内部(或隐或现)的斗争,也没有把妇女(和儿童)当作考察主题和斗争的参与者。[ix]所有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资本论》的有限主题给排除了。但是,如果认为只要马克思写完了论雇佣劳动的著作,这些观点就会在这本书中出现,也是很天真的。
事实上,马克思期待的是“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形式”。〔153〕他本人认为现有的安排是“毫无品位”且充满矛盾的(他指出新社会的奴隶制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认为他将会就这些问题在细节上进行展开,那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够和同时期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超越《维多利亚公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限制女性劳动的《工厂法》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指出“是为了女性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为了她的丈夫劳动,这一事实被提倡该限制的鼓吹者称之为男人的家庭”。(Pujol,1992:p.25)
因此,笔者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一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作的已经足够。这样就成了对历史的复写。相反,我的目的是想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存在发展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简言之,不必非要用折衷的方式给马克思理论添加不同的原理才能创造“实用的”马克思。我的目的当然也不在于用所提出的问题构建一个全面的论述方案;这个方案将由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论者继续研究。[x]因此,此处提出的并不是可能在论雇佣劳动的著作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就其内容提出的问题。
我们以上的讨论看上去似乎稍微偏离了主题。但是,既然我们要研究与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的决定因素,那么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同时要强调的是,那本关于雇佣劳动的未完成的书也很重要。如果对那本书的内容缺乏了解,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永远认为对女性的特殊剥削是非本质且不重要的。如果排除劳动者的“各种决定因素”,只把他们看作是抽象的雇佣工人,那么家长制必然会位居其次。
当然,与资本对立的雇佣工人不仅仅生活在家庭范围内,他们还生活在邻近地区和社会团体中一事实上,他们被资本集中到了特殊的地区和城市,而且分布在不同的国家。(Engels,1845:p.344,p.394)他们不仅仅被划分为男人和女人,还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种族等。一旦我们认识到“各种假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实现人类个体的生产”,那么按照某种依据对雇佣工人进行划分也是很正常的,这些依据包括:年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历史环境以及“所有的人类关系和相互作用,无论这些关系和作用是否会出现互或者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马克思却没有采取这种方法。他的评论局限于身边的直接〔154〕问题,即劳动力价值问题。因此,他承认“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48]对于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必需品标准之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xi]
必需品标准不仅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也有区别。爱尔兰劳动者的状况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这种短工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49]马克思指出,他们较低的必要需求(与英格兰其他劳动者的必要需求相比)反映出了爱尔兰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这种条件使他们的必需品标准维持在这个水平,而他们的生理需求也适应了这个水平。
然而,劳动力价值反映出来的区别并不局限于“人们生活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区别。社会条件不过是“历史的”前提;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永远解释不了相对工资的变化——例如,属于不同群体的劳动者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却趋于相等(可能会上下波动)。依据历史前提的解释方法,“脱离农奴状态时”各种工人群体所处的“条件好坏程度不同”[50]看上去就是一种原罪。
总之,就像必需品标准随时间变化会有所区别的情形一样,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必需品标准也存在区别,这种区别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工人向相反的方向互相斗争的结果。历史前提(在它们会影响社会需求水平的限度内)可以解释为什么个别劳动者不能对资本进行猛烈地挤压;然而,是劳动者当前所接受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前提决定了必要需求的水平。
当然,原理性的东西超出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现实状况。它不仅包括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劳动者,还包括了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例如,除非我们认识到阶级斗争对劳动力价值的主要决定作用,否则我们就会认为男女之间的工资存在区别是因为女性的必要需求低于男性。这样的理论是荒谬的,就好像马克思相信爱尔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总是低于英格兰劳动者一样荒谬。
〔155〕马克思并不是认为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而是认为每个工人都代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整体。这自有其内在含义。由于工人的自我生产产生的人类个体分为不同的种类(需求水平不同则等级不同),而他们能够正常满足的需求水平是斗争的结果,因此,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贫困化现象。[xii]尽管《资本论》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是,只要我们对作为非雇佣工人的工人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讨论的劳动者不是抽象的雇佣工人,而是处于各种决定因素中的人类个体。[xiii]
8.3 生产整体工人的过程
认为生产工人的过程仅仅发生在雇佣劳动之外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认为家庭是劳动者生产进行的地方,那么这个生产过程就是自然的、物质的,而不是社会的。但是,如果工人的每一种活动都从某个特殊方面对他本身进行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显然也应当包括在内。
[51]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3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讨论。某种人类个体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他们拥有对另类商品的需求。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些需求品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也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流通范围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些需求品只能由劳动力获得。因此,资本必然表现为雇佣工人的媒介。
相应地,被生产的劳动者意识到了他们对资本的依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事物不仅有助于建立依赖关系,而且有助于“从属感情”。资本的这种性质是神秘的——“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象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象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52]资本放弃了“劳动的创造力”的权力,“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53]这样对劳动者来说资本就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54]因为它看上去像是所有生产力的源泉。
所有的必要资本,包括固定资本、机器设备、科学技术等都只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55]
因此,马克思注意到,这种转换“社会生产力——这种做〔156〕法在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资本的属性”。[56]总之,雇佣劳动的意向在于向资本贡献能力,因为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它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
这样,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可以利用工人对它的依赖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完成了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出来的工人把资本的需要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
[57]
资本以“多种单个资本”的形式存在。资本的这种存在形式与单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共同促成了工人的分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依赖于整体资本,还依赖于单个的资本。在资本竞争中,工人群体尽力满足需要,以帮助雇佣他们的单个资本取得胜利。这样,在竞争中就出现了一种典型的倒置——工人的竞争不被看作资本间竞争的形式和资本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反而资本竞争自发地表现为工人的竞争,是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手段。资本整体实际表现为众多单个资本,这就奠定了不同企业(一国之内的或跨国的)的工人进行分化的基础,也奠定了工人在竞争之战中向资本“屈服!的基础。[xiv]〔15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中把握了工人分化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47年写到:
“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发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谅解并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阶级。由于他们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换句话说,这使得工人们的目光短浅到这样这种程度:在他们眼里,他们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援军。雇农和短工维护贵族或雇用他们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师傅为移转。工厂工人听凭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58]
〔158〕‘简言之,资本趋向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即把资本-的需要看作是“显而易见的自然规律”的雇佣劳动。然而,因为资本生产的工人本身就是与之对立的,所以工人对资本统治的抵抗受到压制,工人的分化也不断发生。与资本对立的工人产生于劳资关系之外,他们也为教育、传统和习惯作出了贡献,而这些教育、传统和习惯使资本需求看上去是理所当然的。总之,“所有的人类关系和作用都影响着物质生产,并且或多或少地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韦尔赫勒姆·瑞克(wilhelm Reich)通过吸收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强调了家长制、国家独裁统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父亲的独裁反映了他的政治作用并且显示出家庭与独裁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中,父亲所处的地位与在生产过程中他的雇主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而且,父亲在家庭中通过独裁将这种服从的态度复制给他的后代,尤其是他的儿子。”(Reich,1976:p.49,pp.14~15)
工人作为非雇佣工人的被生产在很多方面对资本起到了加强作用。我们看到,资本对工人进行分化和分工的能力是其存在的条件。然而,在劳资关系之外生产工人的过程确保能够把他们作为不同的人类个体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已经依据性别、年龄、种族和国籍(或其他方面)对雇佣劳动进行了不同的划分。这样不仅增加了工人统一起来的困难,而且为资本利用这些区别提供了契机。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爱尔兰工人的情况。历史因素导致他们的工资低于英格兰工人,他们为了得到这些较低的工资进行劳动。发展趋势是降低英格兰工人的工资;马克思注意到,这样做会加强资本的统治。然而,从实质上说,问题不仅仪在于工人之间的普遍竞争会削弱其在劳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力量:
在英国,每个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都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英格兰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英格兰无产者痛恨爱尔兰无产者,因为爱尔兰无产者的竞争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标准……他们把英格兰工人看作是英格兰统治爱尔兰的愚蠢的工具与帮凶。
因此,在相互竞争的劳动力出卖者之间不仅存在分工,而〔159〕且存在为了强化所有这些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特征、社会特征和国家特征)进行的“对抗”;这些“对抗”使爱尔兰工人和英格兰工人成为不同的人类个体。在资本主义的正常工作方式下,区别变成了对立。在这种对寺中,马克思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59][xv]
但是,回想起资本加强霸权的所有方式,我们不确定能否把工人自身的这种特殊分化看作是资本维护其力量的唯一“秘密”。一旦我们把工人作为考察主体并摒弃抽象雇佣劳动的概念,这个问题就会引起注意。一旦我们想到与资本对立的工人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想到工人的所有决定因素,我们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曾经认为工人能够超越资本?〔160〕
※ ※ ※
注释
[i] 参见马克思(Malx,1977:pp.739~40),从资本家作为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角度出发。
[ii] 例如,在讨论资本家自身花费在商品流通上的时间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在交换中损失的时间,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劳动时间的扣除。他所以是资本家,即资本的代表,人格化的资本……流通时间——就它占去资本家本身的时间来说——跟我们的关系,就像资本家同他的情妇消磨的时间跟我们的关系一样……资本家在这里如果不是作为资本,就同我们绝对无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9~140页]
[iii] 马克思也指出:“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iv] 从工人角度来看工作日的含义超越了从资本角度定义的工作日。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剩余价值率可以被看成是剥削率(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的一个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若工人进行为自己的必要劳动(即私人劳动),则剥削率要比剩余劳动力低。参见莱博维奇(Hebowitz,1976a)。
[v]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总结道:“通过榨取工人子女……来得到满足的”,这是产业工人中高出生率的一个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4页)南茜·弗尔博的观点与马克思的相当一致,她强调了童工法案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均家庭规模缩小之间的关系。参见Ferguson和Folbre—(1981:p.323)。
[vi] 如,考察庄园主从要求农民提供劳动服务转向要求货币支付这一让渡带来的长期影响。
[vii]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象童工法案和对妇女和儿童工作日限制的立法没有为整体工人带来利益。
[viii] 对于父系社会和性别、性格(gender.personality)的社会构造之间关系的研究,乔德瑞(Chodorow)作了开创性的研究(1978)。
[ix] 福格尔(Vogel,1983:p.61)指出,在所有马克思关于奴隶制的论述中.妇女和儿童始终都被形容成“被动的受害者而非历史的参与者”。
[x] 尤其是,对父权的关注要远远超出对父系社会形成基础的考察,而且这一关注适当地包含了对一些在此不能详述的问题的考察,如对于强奸的发生和影响。在此我并没有融合马克思女权主义者的最新学术思想,但关于这一思想的有意义的最新的评论可参见(Camfield(2002)和Vosko(2002)。
[xi] 马克思也指出了“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的不同在解释工资的国别差异时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3页)
[xii] 需求的不同级别——甚至“必要需求”(从广义来讲)也是如此——会产生不同的悲惨化程度。换句话说,因为工人正常情况下,可满足的特定需要会由于他们斗争的成功程度(和他们个人需要的等级)而不同。这两种类似的情况可在一两个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图上标出(如图3.1),该图分别表示了不同的“幸福点”(bliss point)和不同的真实工资水平这两种情况。
[xiii] 与工资差别相关的其他问题在此并没有讨论,可参见Fine(1998),尤其是第7章;也可参见Saad-Filho(2002,ch4)。
[xiv] 处于竞争性厂商中的工人是不可能合作的,他们陷入了“囚徒困境”。
[xv] 参见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书信(1870年4月9日),接着,马克思在论及美国南北战争时同样提及:“爱尔兰人认定黑人是危险的竞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4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3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l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一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15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一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4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一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21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22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48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3页注释。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3页。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页注释。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7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3页注释。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2页。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6页注释。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3页。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页注释。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6~537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8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5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5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一12I页。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5~80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6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