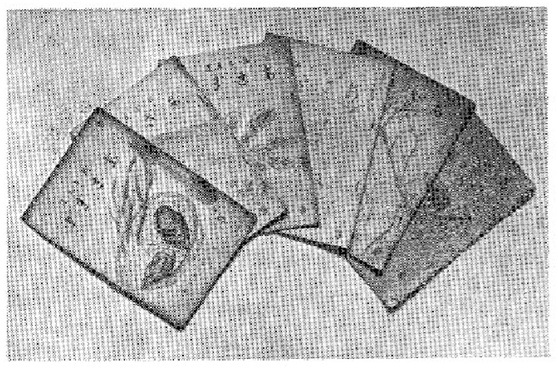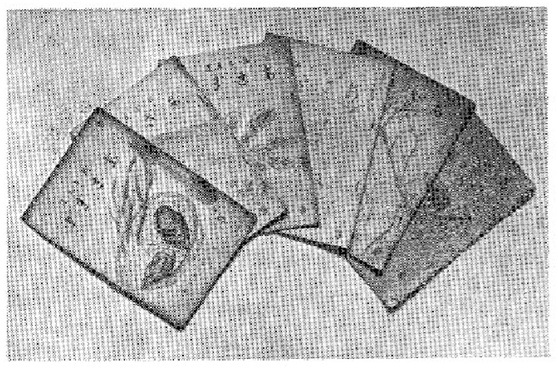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1981)
第九章 工会运动的覆灭与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落入了配合战争的罗网
就在我们继续开展活动的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在不断加剧。每天收到的报纸上都配着中国地图,每当城市陷落,就会在头版上大肆渲染。大城市陷落的时候,政府就会组织提灯游行,用“胜利了!胜利了!”的消息来激励国民。然而,“大本营”[1]的声明,只不过是在不断地欺骗国民罢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抵抗正在使战争变成持久战。蒋介石撤退到了偏远的重庆。在辽阔的中国,日本只能控制一些战略要地和它们之间的交通线,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和军需物资投入中国。在一部分国民中间,厌战的情绪开始出现。
但是,大部分国民并不知道真相,所以只能沉默地服从政府与军部。
政府制定了“物动计划”[2](依照《国家总动员法》,将物资和劳动力全部集中于军需产业的计划),打出了“奢侈就是敌人”的口号,下令禁止生产一切非必要产品、非紧急必需产品和奢侈品。由于没有汽油,汽车只能烧木炭和柴火。街上立起了许多标语牌,写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日本人就不该奢侈”、“女人不要烫发”、“把袖子剪短吧”。妇女只能穿扎腿套裤[3]。
像我们这些在民用产业工作的工人,只要接到俗称“蓝纸”的国民征用令,就会被拉到军需工厂工作。政府以“圣战”的名义,强迫劳动人民忍耐这一切。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六月,对外侵略达到了新阶段,嘴上标榜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实则翼赞侵略战争的社会大众党自行解散了。政府对它施加压力,说它的党名的阶级意味太强烈,要求它改名,否则就要取缔它;它顶不住压力,就只好解散了。在解散仪式上,他们遥拜皇居、齐唱国歌、祈祷皇军武运长久、为英灵默祷。就连如此积极配合战争的社大党,都不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当年十月,大政翼赞会成立了。它的核心是政府官僚,在中央和地方设有各级组织,又有民间领袖加以辅助,政府创立它,是为了制造一张罗网,把国民网罗起来,迫使国民支持战争。
民间的自主团体都被强行解散,并入大政翼赞会。大政翼赞会为了强化自身组织,还在街道一级成立了“邻组”[4],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在参加邻组的例会时,跟警察有关系的头头就会耀武扬威地叫大家做这个做那个,什么收集废品啦,节省粮食啦,义务清扫街道之类的,美其名曰“勤劳奉公”,甚至还强迫大家带上水桶、灭火器,去参加防空演习。还强行摊派国防捐款和战时国债,叫你交多少就得交多少。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就连私生活也要遭到邻组组长的监视。在国际上,形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德军在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九月一日凌晨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状况下,柴田努力让活动家们理解当前形势。他经常到书店去,虽然在战时很难找到介绍国际形势的书,但是,只要有这种书,他就一定会买下来。他通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了解了中国红军的本质,红军的严明军纪,使他确信红军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经常跟我们谈起八路军。活动家们受主流报纸的报道影响较大,所以他便努力使他们了解中国和德国的真实战况。
到了这个时候,侵华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对决——的一部分,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把中国这个烫手山芋抱在怀里的日本就算想要谋求和平,也不得不将问题放到全世界的层面上来解决。
军部不得不进行最后的豪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日军以切断敌军补给线为由,向苏军挑起武装冲突,却遭到了惨败。而这一次,为了确保石油和其它资源,日本又要向包围自己的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开战,给予这些国家猛然一击,以此争取和谈的一线生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日本从泥潭中挣脱出来。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内的镇压体制,更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战争,必须极度扩张生产力,所以必须迫使工人阶级配合战争。
产业报国会的组织化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厚生、内务两省的次官下令,民间企业必须配合政府,把所有人组织进产业报国会。特高警察强行解散了日本的所有工会,炮制了政府的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让产业报国会吞并了所有工会组织。
当时负责代表俱乐部同警方交涉的山县说:
“自从俱乐部在芝区田村町设立办公室之后,我就负责代表出版工俱乐部同警方交涉。每个月我都要把跟本部和芝支部有关的集会申报表向警视厅和爱宕警署上报一次,集会结束后,还要把议事内容、参加人数等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而且,俱乐部发行的机关刊物,每个月也要拿给警视厅审阅科检查一次。这项工作很费时费力。因为从事这项工作,我在哪个印刷所都干不长。不是在提交材料的那天上班迟到,就是不得不向公司请假。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初,我接到了爱宕署的特高警察发来的‘请求’:‘产业保国会很快就要成立了。所有的工会都要进行建设性的解散。不如你们也像其它工会一样,解散之后再加入产业报国会吧?’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柴田,他说:‘尽管对方这么说,但我们也不必马上答应照办,先看一看再说。’于是我就对警方说:‘我们是联谊会,不用加入产报吧?再说,每个会员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属的公司的产报了。’以此来拖延时间。警方以官僚的独特作风,以为可以利用高压逼迫我们就范。警方重申:我们必须解散组织、加入产报,一开始还是恳求,最后变成了恐吓:‘再不加入产报,就把干部统统抓起来。’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能再糊弄下去了。我就回复说:‘总之,我们得先跟大伙商量一下,到月底再答复,请你们先等等吧。’然后我就回去了。”
那一年,警察是如何执行厚生省和内务省的决定、将日本的工会全部解散的呢?就用内务省当时的资料来说明吧。
昭和十五年 被解散的工会[5]
(会员一千人以上的工会)
二月 邮电从业员同盟(逓信従業員同盟)
三月 东京市从业员工会(東京市従業員組合)
四月 邮电从业员工会(逓信従業員組合)
五月 东京瓦斯工会(東京瓦斯工組合)和另外一个工会
六月 东电职员同志会(東電職員同志会)和另外四个工会
七月 日本劳动总同盟、日本工会会议、东京交通工会(東京交通労働組合)和另外十二个工会
八月 东京汽车鹤见从业员工会(東京自動車従業員組合)和另外四个工会
九月 日本海员工会(日本海員組合)、日本港湾从业员工会(日本港湾従業員組合)和另外四个工会
十月 日本制陶工会同盟(日本製陶労働組合同盟)和另外一个工会
十一月 名古屋市电从业员俱乐部(名古屋市電従業員倶楽部)和另外一个工会
从此以后,直到终战为止,日本的工会在纸面上便不复存在了。
仅存的最大工会——总同盟直到最后仍想保存组织,但是,总同盟的大头目松冈[6]、西尾被叫去警视厅,在那里有人威胁他们,说如果不解散的话,就没有好下场,于是他们只好忍痛解散了总同盟。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就连这种鼓吹劳资妥协的右翼工会都不被允许存在了,被迫一一解散了。
对于总同盟的头头来说,这反倒是因祸得福:总同盟解散后,他们没能搭上产业报国会这趟车,所以在战后才能躲过“公职追放”[7]。
贯彻到底的解散令
总之,在厚生省和内务省的恐吓下,总同盟发表了悲壮的声明,然后就解散了。被粉饰为“建设性的解散”的强制解散命令,就这样得到了贯彻。工会的财产被强行处分,工会存在过的痕迹也都被抹杀了。下面这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
海员工会解散后,兵库县的海员工会会员们聚集起来,在日本海员工会会馆前的空地上,立了一块“日本海员工会纪念碑”,可是兵库县特高警察却来找碴,说这块纪念碑居心不良,想要永久性地宣示工会作为阶级组织的意义,而且从立碑的地点来看,也会促使前工会会员和海上劳动者重新萌生工会意识,因此便强行把纪念碑上的“日本海员工会纪念碑”改成了“日本海员会馆纪念碑”。
特高还加紧了对解散后的团体的监视,前工会会员的聚会,如果被特高得知的话,马上就会被特高驱散。在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于一九六五年发行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第四十三页上,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于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工会的废墟上成立了。它组织起了五百五十万工人,然而,它根本不像工会,而是被内务省和厚生省操纵的、用于战时动员和压迫的庞大官僚机构。产报驱使工人从事军需生产,对资本家来说,它是能够保证无限制剥削的奴隶劳动组织。这样一来,战争体制就完成了,最后,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在接到解散命令之前,柴田就预料到了这件事,他说过:
“日本工人运动的右翼干部协助军部,瓦解了工会组织,把工人出卖给了敌人。许多团体因此被强行解散。俱乐部恐怕也会接到解散命令。在那种情况下,俱乐部由于以前的活动,肯定会被当成‘赤色’组织。无论如何,俱乐部都必须保存自己。为此必须顺应时局,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形式。工人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提高阶级觉悟。不要拘泥于形式。接下来,我们要么以生活为基础而开展活动,比如改为消费合作社,要么改为印刷业者的技术研究会,这样做的话,无论是谁,都会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
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又叫大家读一读关于英国的罗奇代尔合作社[8]的书。然后我们立即开展工作,努力把运动转到这个方向上。我们跟当时住在山手那边的贺川丰彦[9]的消费合作社进行交涉,弄到了木炭的配给证,跟附近的木炭商人一起去枥木县宇都宫的飞机场旁边,买来两货车的木炭,运回东京后,一车分给木炭商人,另一车分给芝、神田、京桥、深川的俱乐部会员。白石、杉浦、田口用排子车和两轮拖车帮助分发木炭。我们还帮会员修理家里的破损的障子,这项工作主要是由芝支部的江口健治郎[10],京桥支部的小泉孝一[11]、原田米三[12]、泷泽保二等会员来做的。
此外,为了争取经营者的支持,我们还打算成立技术研究会,为此我们以“如何提高作为手工业的印刷企业的效率”为卖点,跟神田区的三秀舍高管岛诚、芝区的爱宕印刷高管会面,讨论了排字的设计等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印刷业经营者的赞同,我们就要努力建设一个合法组织,再把整个俱乐部并入其中。柴田还在新富町[13]的餐厅里,跟京桥滨田印刷的滨田仙松[14]举行了会谈。当时跟柴田一同出席会谈的小宫说,在酒席上跟经营者一起谈话,对清廉正直的柴田而言,应该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吧。
我们还要继续举行俳句会和旅行会等活动,但并不是作为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作为当时被厚生省当作国策大力鼓吹的“余暇善用”运动的一部分来开展。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减小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小宫在三钟印刷工作,他拿着社长开的介绍信,找到东京市劳动局,请课长写一篇稿子,就说海之家的活动“有益于余暇善用、身心锻炼,适合当前时节”,再登在《俱乐部新闻》上。一般来说,劳动局的人是不太愿意给我们写这种稿子的。所以小宫觉得这事没戏,但柴田说:“你先把文章写好,再请课长署名就行,反正我们要的只是他的官衔。”课长勉强在文章上签了名。另一方面,为了在接到解散命令之后仍能保存力量,柴田还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准备把俱乐部拆分为旅行会、俳句会和读书会。
寻找保存俱乐部的方法
在做准备的时候,柴田也考虑了遭到镇压的情况,于是他便同少数领导干部谈话,让他们对镇压做好心理准备。
“我认为,我们不会遭到镇压,但是,思考一下在遭到镇压时该怎么办,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因为,在遭到逮捕时,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无法同警察斗争。万一被抓走了,绝对不能供出组织的情况。好比说,警察要打你十下,你要是为了少挨两下打就招供的话,那大家就都完了。你可能会想:‘这么点小事,说出来又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这样想,那就糟糕了。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招供了,不管说的是多么小的事,都会导致另一个同伴陷入危险。所以千万不能招供。只要心中满怀阶级仇恨,无论什么样的酷刑都能挺过去。在同刑讯斗争时,必须怀着这样的信念:每挺过一次酷刑,能够肩负起下一个时代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那年(一九四〇年)八月底的一个星期日,在出版工俱乐部于江之岛设立的海之家里,来了大约三十位活动家。他们是来参加会议的,而这场会议将决定出版工俱乐部的存续。俱乐部存续的基本方针,已经在锦丝町的柴田家中定下来了。干部们前一晚就住了下来,商量好了第二天的对策。我们事先在活动家当中做了动员,谁跟谁一起来都安排好了,所以出席人数是三十人。会场里还有同盟通信社的记者O氏。但O氏并不是会议的正式参加者,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偶然来到这里,就碰巧参加了会议。我们请他介绍国际形势。他讲完后,是留在会场,还是马上回去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最后,柴田提出了事先定好的基本方针:
“我自己根本不想让俱乐部消失。出版工俱乐部要是没了,此前围绕着它团结起来的工人,又该依靠什么活下去呢?产业报国会吗?那是让工人充当战争道具的组织。看一看就知道了,那就是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根本不允许工人进行横向的联络。就是为了这些工人,也必须保存俱乐部,让俱乐部承担起把各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的任务。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知道大家的想法基本上都没有改变。然而,虽说要保存俱乐部,但俱乐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动了。我们要按照警方的要求,在形式上解散俱乐部。但是,俱乐部之前做的各项工作,要分散开来,继续进行下去,这样就能在实质上保存俱乐部。好比说,把现在的旅行部改为旅行会,把俳句部改成俳句会,把读书部改成读书会,让现在的俱乐部会员加入到各个会里去,这样就能保存现有的组织。各个会之间的联络,必须小心地进行,这样做多少会有一些危险,但运动不可能没有危险。大家说,干不干?”
按照前一天晚上的碰头会上的部署,有几个人发言表示赞成他的意见,然后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仔细一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日本在中国战线上陷入了泥潭,为了打破僵局,它要“举国一致”地向美英开战,为此,它把彻底消灭阻碍战争的工会定为国策,而这次会议的决定,便是对这一国策的反抗。深思熟虑的柴田,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就冒冒失失地决定保存俱乐部。我们本来打算向全体出席者仔细介绍形势,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决定保存俱乐部,可能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使他们加强对抗镇压的觉悟,然后再让他们自主地做出决定。但是,如果这样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否决保存俱乐部。在这种窘境中,柴田恐怕是非常难熬的。他衷心地希望镇压不会真的发生。后来,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们遭到了镇压、逮捕和监禁,但我仍然认为,会议做出的不服从政府的解散命令、继续保存俱乐部的决定是正确的。参加江之岛会议的俱乐部会员,包括我在内,战后大多继续活跃于工人运动,或是为了建设民主印刷所,而参加了民商[15]活动或其它民主活动,我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因为这次会议是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所以,在当天的参加者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意识到,俱乐部的存续一旦暴露,就会导致全体出席者被捕。由于俱乐部此前的活动并没有遇到多少麻烦,所以大家也都觉得比较安心。
转入地下活动的出版工俱乐部
出版工俱乐部在本部办公室举行了解散仪式,不过这只是装装样子罢了。爱宕县特高警察也出席了仪式。佐藤次雄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在海之家举行的活动家总会结束后,大概是八月中旬吧?在芝区办公室举行了解散仪式。参加解散仪式的干部和活动家,以白石为首,来了很多人。有个没见过的穿西装的男人,他是爱宕县的特高,他叫白石把参加者的名字全都记下来。白石一边看着每个人的脸,一边把名字写下来,然后交给那个男人,仪式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结束后,白石对我说:‘一起回去吧’,然后我们就从新桥出发,去了银座。由于战况吃紧,物资匮乏,商店橱窗里空空如也。白石说,他妻子怀孕了,就买了一些黄油和奶酪给她吃。然后我们去了银座六丁目的‘巴西咖啡’(ブラジルコーヒー),进门后,白石看着我的脸,安慰我说:‘刚才的名单全是我瞎编的,我没写你的名字。’但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发现,面前的白石没有了以往的活力,显得非常沉痛哀伤,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从那时起,白石暂时退出了俱乐部的活动,原因不明。但是,见证了俱乐部解散的白石,在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为晓印刷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讲过,在俱乐部被强行解散之前,以总同盟、东交为首的许多工会,就已经自发地、或是在警方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了。到了十一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了,会长是平生釟三郎[16](国铁会长),理事长是汤泽三千男[17](前内务次官),工作人员由特高、官僚、军需工厂的劳动事务负责人,以及三轮寿壮[18]、菊川忠雄[19]等前社大党干部充当。他们有意识地切断了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从此以后,工人就被关进了名为“战时状态”的监狱,被当作奴隶使唤。
战时的镇压越来越严酷。俳句、诗歌、漫画等方面的民主团体、文化团体都遭到了镇压,就连基督教、救世军也得宣布自己的立场是“纯正的日本基督教”,不然也要遭到镇压。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八月,新协剧团[20]遭到镇压,村山知义[21]和另外二十六人被捕,随后新筑地剧团的八田元夫[22]等十四人也被逮捕,剧团也被迫解散。对劳动人民的管束和严厉镇压,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而做的准备。
军部在辽阔的中国,陷入了连战略要地及交通线都无法确保的窘境,它在极度焦躁之中,以切断补给线为由,把战线延伸到了中国背后的印度和缅甸,然后,日本为了打破英国、美国、荷兰的经济封锁,又进一步向法属印度(现为印度支那)、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进攻,为了做好同美英开战的准备,日本准备进一步压榨国民。
于是,在越来越黑暗的形势中,俱乐部会员在特高眼皮底下埋头工作,努力修复被产业报国会切断的工厂与工厂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芝区成立了“日出旅行会”(日の出旅行会),在京桥、深川成立了“曙旅行会”,在神田成立了“若叶旅行会”;又在神田成立了“青桐吟诗社”(あをぎり吟社),在芝区、深川、京桥成立了“朝雾吟诗社”(あさぎり吟社)。为了把这些团体联系起来,还设立了简易图书馆,它把文库设在柴田家中,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开展活动,只是俱乐部会员不能像以前那样集合起来、齐心协力地做事了。
活动开展得很顺利。“若叶旅行会”和“曙旅行会”为了筹措旅费,实行了月费制度,两个旅行会共同制定了旅行计划。不过在招收会员时,两个旅行会是分开行动的。
地下活动
当时日本完全倒向德国,引进了德国候鸟运动[23]的休闲活动。纳粹为了吸引青年,打出了“劳动就是欢乐”的口号,利用候鸟协会组织青年过集体生活,组成许多队伍,一边旅行一边进行劳动动员。我们的两个旅行会就伪装成候鸟协会的拥护者,动员许多工厂的青年工人登山。
活动家们为了制定多个登山项目,请喜欢登山的人做了实地调查,然后再经过集体讨论,定下了ABC三个登山项目。A项目是规模较大的登山活动,时间为四天三夜,费用也很贵;B项目也是登山活动,需时两天一夜,费用比较便宜;C项目是当天往返的远足活动,很适合大众;各个旅行会都制作了用手工印刷的、篇幅在五到六页的机关报,在上面刊登了地图和路线的说明,发给各个工厂,募集参加者。
奥多摩的御岳、里高尾[24]都很适合C项目。在集中攀登景信山[25]的时候,“日出旅行会”从高尾出发,“曙旅行会”从小佛出发,“若叶旅行会”从相模湖一带出发,一齐登山。
各个旅行会的队伍在碰头会上事先估算好几时几分登顶,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集合在一起,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初次见面的人相互交换点心,一起煮味增汤喝,聊聊各自工厂的事,然后又举行合唱,表演才艺,玩得很开心。下山时,我们是按照各自的路线走的。有时还会唱起劳动节的歌曲。通过这些活动,旅行会的会员们保持了联络。
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方法,努力把老会员集结起来、并维持印刷工人的组织的。
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活动:
“我是‘青桐吟诗社’的负责人,当然,我不只负责俳句活动,还要协助‘旅行会’,还要拿着‘读书会’的书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做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各个团体的负责人的住址和姓名都是错开的,但在根子上是牢固地连成一体的。
“我们的神田区办公室(也就是根据地)设在牛込区(现在的新宿区)新小川町的南云富吉的家里,小宫和大桥都在南云家租房住。当时能商量的会员有小宫、南云、大桥、谷口、渡边武、佐藤、青野义雪
[26]等六七人。
“组织体制的转换进行得比较顺利,大部分的老会员应该都被吸收过来了。尤其是俳句会进展喜人,发展了不少新人。在开展俳句和其它活动时,我们都必定要把协助者给组织起来。在制作俳句杂志时,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每一期杂志的封面,都是由在宫本印刷工作的排字工木下
[27]和在冢田印刷工作的拣字工中村画的;从整理原稿到誊写、印刷、装订、分发,都找了好些人来帮忙,在一同活动的过程中,大家的关系变好了。凡是物色到有前途的人,就在下班时跟他一起回家,请他去喝咖啡,边喝边了解他的生活还有想法,几个人一起有意识地做他的工作,系统地帮助他提高觉悟。为此充分利用了读书会里的范围广泛、数量众多的书籍。经常给《青桐》杂志投稿的有七八十人,它的印量是三百本左右。就算不投稿也没关系,只要是读者,我们也一定会送去杂志,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份杂志是把各工厂的读者和我们连接起来的纽带,是联络工厂的武器。通过读者的推荐,这份杂志获得了新的读者,在尚未建立联系的工厂里也赢得了读者。
“每隔两三个月,我们就会举办运座,虽然是在神田桥的荞麦面店的二楼举行的,但搞得也挺盛大的。由于会费便宜,而且大家基本上都能拿着作为奖品的生活必需品回家,所以大家都赞不绝口。大家不是印刷工就是活版工,聚在一块,自然就会谈起工厂的事,对工厂里的工人的生活和活动也就更加了解了。俳句写得好的只有渡边武,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临时充当‘俳句家’,所以写俳句对他们来说恐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虽然买来《岁时记》学习,但还是很难成为俳句家,心里难免会有‘俳句算什么玩意’的想法。”
在京桥、芝区发行的油印的俳句杂志《朝雾》,主要是由杉浦、田口、福田等人负责的。杂志的封面,是先由擅长绘画的河崎画出线稿,再由活动家们上色的,从誊写到印刷,都是由老会员们合力完成的。最近找到了“朝雾吟诗社”发行的六本机关刊物,在战争期间,田口仲子[28]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三卷第三号是在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三月一日发行的,发行地址为芝区田村町二-一〇岩田宅,这证明了这份杂志连续出版了三年。在“志友芳名簿”上,记录了十四名同仁、六十九名志友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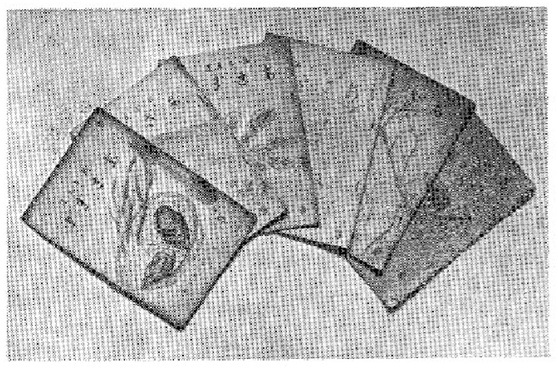
最近发现的当时的俳句杂志

青桐吟诗社的吟诗会(1941年,镰仓)
“朝雾吟诗会”的运座会经常在爱宕山的“藤よし”餐馆举行。“青桐”、“朝雾”两个吟诗会也在柴又、镰仓、池上本门寺联合举办过吟诗会。
参加这两个俳句会的人,分别属于好多个工厂,所以我们也能同大工厂建立联络。
躲避警察的耳目
佐藤介绍了出版工俱乐部伪装解散后的活动:
“改成旅行会后,我们经常去爬山。不仅如此,我们自己也被山的魅力给迷住了,甚至憧憬起了在冬天登山。星期六晚上出发、星期天晚上回来的行程,很适合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甚至有过一个月爬山四次的记录。
“但是,我们绝不会一个人去爬山,就算是只有几个人也好,我们也一定要邀请协助活动的人或是觉得有前途的年轻人一起去。
“神田、京桥和芝区的各个旅行会,会联合举行登山活动,攀登人人都能登上的阵场山、小佛岭
[29],每次的参加者有五十人左右。在登山的准备活动中,会有一些年轻的新人加入进来,在登山过程中,我们就让这些新人照顾参加者、鼓励他们积极行动。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攀登富士山的活动。
“随着活动走上正轨,事情也变得忙起来了,就得转移到比较方便开展活动的工厂去,于是我跳槽去了小川町的秀英社,而铃木君就留在三秀舍。
“每天晚上,我都要经过饭田桥,走去南云家。在我们当中,南云年纪最大,我记得比我大六七岁。他体格比较健壮,每当我露出丧气的神色时,他都会过来找我谈话,帮我恢复自信,给我鼓劲打气。他在狱中由于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战后代表日本共产党的新小岩支部参加了江户川区议会选举,但是落选了,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七日病逝。
“大概是在初夏的时候,我跟往常一样,到柴田家二楼的书库去取书,拿去给订了书的读书会会员看,拿到书后,在回去的路上,在锦丝町站附近的十字路口的派出所,被巡警拦下来盘问。由于事出突然,我又是第一次被盘问,所以巡警叫我把包袱打开时,我就照做了。包袱里放着石川达三
[30]的《结婚的生态》
[31],还有《多甚古村》等好几本书,由于书装得太多,包袱鼓鼓囊囊的。
“巡警问我:‘你背这么多书是要干嘛?’我就回答说:‘我给读书会的会员送书来着’,巡警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就不管我了。我走上通往锦丝町站台的楼梯时,有个目光锐利的刑警在盯着什么,我这才觉察到可能出了什么事,所以警察才会布置警戒线。
“第二天,我先跟小宫谈过话,又去找柴田,柴田认真听了我的话,然后说:‘你不该提到读书会的。读书会经常是用来掩护政治活动的借口,那个巡警或许没看出来,但如果是特高的话,一听就明白了。’意思大致是这样。
“我吓坏了,他又对我说:‘不用太紧张。不过,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才是。’然后我们就谈别的事。打那以后,我就买了帆布鞋,还准备了衣服。”
田口说,在分发读书会的书时,为了避免引起警察注意,他换上了登山时穿的衣服,把书装在登山包里。
在黑暗的战争年代,不管政府怎样加强镇压,对战争的不满情绪还是在底层国民当中蔓延开来了。人们在碰面时说出反战言论,或是用“煽动性文章”(不穏文書)来宣泄怒气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些文化活动持续到了第二年。

若叶旅行会越过那须白河(1941年1月)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一月,若叶旅行会从那须高原出发,越过了白河[32];同年五月,又去了大菩萨岭[33]。日出旅行会在同年五月,从三峰出发,攀登云取山[34];同年七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攀登富士山;同年八月,去奥武藏高原[35]旅游;同年九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去正丸岭[36]旅游;同年十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前往志贺高原,翻越涉岭[37]。一九四二年一月,曙旅行会到赤城山[38]旅游。同年一月,日出旅行会去凤凰山麓[39]游览;同年二月,若叶旅行会去了升仙峡、增富温泉[40]等地。通过这些活动,维持了青年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
在物资匮乏、自然也没有多少钱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就把登山的装备给搞全。我们先是扎绑腿,然后再慢慢凑齐了帆布登山包、登山镐、踏雪套鞋、防滑钉等装备。田口买了双鲨鱼皮做的靴子。大家揶揄他,“不怕被老鼠咬坏吗?”不过他非常爱惜这双靴子,可是,在游览积雪的凤凰山麓的途中,靴子却破了个意想不到的大洞。为了加强登山安全,田口和中山春太郎[41]举行了技术讲习会,还买来德国的登山书籍学习。大家还看了《勃朗峰上的暴风雪》[42]等电影,然后就开感想会,相互学习团结的精神以及一个人要想登顶,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等道理。
我们举办这些活动,是想以此来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情况发生。有些青年完全被山的魅力给迷住了,别的什么都不管了。
在严酷镇压下残存的妇女组织
俱乐部的各个部门分开活动之后,只有妇女部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组织形式。领导妇女部的小宫和田口起初打算把妇女部解散,并入旅行会。于是他们去找柴田商量,柴田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做,应该再仔细考虑一下。现在日本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就算她们活跃起来,也不会被人们注意到,这就是现在的状况。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还是继续保存妇女部比较好。可以换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名字。你们讲过的‘大和抚子[43]’这个词,现在很流行。不如就拿它来当名字吧?内容才是关键。只要内容是属于工人的,那就没问题了。”小宫和田口就把女会员集中起来开会讨论。然后就成立了“抚子和睦会”(撫子むつみ会)。
妇女部是以西田富子、水野静江[44]、八木絃(八木いと)[45]等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她们出了一份油印的通讯,每一期有十二到十六个版面,封面是川崎画的,卷首语是田口写的。以“抚子和睦会”为名的妇女部集结了大约六十名会员,她们在南多摩丘陵和向丘举行远足,还办了厨艺学习会、戏剧研究会,在严酷的镇压下保存了组织。水野静枝[46]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到现在还记得,柴田说过:‘人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必须为世界做点什么。不光要让自己过上好生活,还要让大家都过上好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说世界变得美好了。’那个时候,生活真的很充实。我觉得人生很有成就感。不过,老实说,我记得活动是很辛苦的。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午休时还得自己掏钱给会员打电话,每天晚上要到十一点以后才回到家,母亲经常责骂我,说要跟我断绝关系。我跟西田谈过好多次,都说不干了,要退出俱乐部。我们打算领到工资后,就把大部分工资用来照顾家里。父母嘴上虽说要断绝关系,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女儿做的不是坏事。活动很辛苦,可是我们还是忍下来了,这大概是因为从俱乐部活动中得到的教导吧。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都是竭尽全力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对青春无怨无悔。”
这样的活动并不轻松。在战争期间,无论什么活动都要遭到特高的监视,所以,我们能够持续活动这么久,简直可以说是奇迹。
[1] 大本营(大本営/だいほんえい)是日军的战时最高统帅部。——中译者注
[2] 全称“物资动员计划”(物資動員計画/ぶっしどういんけいかく)。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确保物资优先分配给军需产业,而对物资进行全面管制,便制定了这个计划。——中译者注
[3] 扎腿套裤(もんぺ)是妇女在下田劳动时穿的一种工作服。——中译者注
[4] 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的村落内就存在着五人组、十人组之类的村民互助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战局日益紧张,日帝当局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1940年9月11日发布《邻组强化法》,将原先的居民互助组织改为“邻组”(隣組/となりぐみ),以五户到十户为一组,进行居民动员、防空、思想管制等活动。类似于中国的保甲制。——中译者注
[5] 内务省警保局编,《社会运动的状况》(社会運動の状況),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原注
[6] 松冈驹吉(松岡 駒吉/まつおか こまきち,1888年4月8日——1958年8月14日),生于鸟取县岩美郡。高等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到处打工。1906年加入基督教。1910年进入日本制钢所(日本製鋼所)工作。1914年加入友爱会。1921年友爱会改组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后,1925年担任总同盟中央委员,1932年担任总同盟会长.1946年8月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労働組合総同盟),并担任会长,同年代表日本社会党当选国会众议员,1947年5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出任众议院议长。1958年因肝病去世。——中译者注
[7] 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于1946年1月4日发布《关于褫夺不适合从事公务者的公职的文件》(公務従事に適しない者の公職からの除去に関する件),要求将战犯或积极配合军国主义的人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驱逐出去,通称“公职追放”(公職追放/こうしょくついほう)。到1948年5月为止,有二十多万人被开除公职。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司令部逐步缩小了清洗范围,1952年彻底废除了“公职追放”令。——中译者注
[8] 罗奇代尔公正先锋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于1844年成立于英格兰兰开夏郡罗奇代尔市,它是最早的消费合作社之一,它提出的“罗奇代尔原则”是现代合作社运动的基石。——中译者注
[9] 贺川丰彦(賀川 豊彦/かがわ とよひこ,1888年7月10日——1960年4月23日),生于兵库县神户市,幼年失去父母,15岁时家庭又因兄长生活放荡而破产。1904年在上中学期间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从1909年起,开始在贫民区传道和经营慈善事业。1919年参与创立友爱会关西劳动同盟会(友愛会関西労働同盟会),并出任理事长。1920年发表自传体小说《越过死线》(死線を越えて),引起轰动,同年创立神户消费合作社(神戸購買組合),还创办了《基督教新闻》(キリスト新聞)。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农民协会(日本農民組合)。1926年参与创立工农党,并担任执行委员,当年年底工农党分裂时退党。三十年代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二战爆发后参加“国际反战者同盟”(国際戦争反対者同盟),1943年因遭到宪兵队调查,退出国际反战者同盟。二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晚年致力于世界联邦运动。——中译者注
[10] 原千代田印刷工会执行委员。——原注
[11] 原行政学会印刷执行委员。——原注
[12] 原土井印刷执行委员长。——原注
[13] 新富(新富/しんとみ)是东京都中央区的一个地名,原属京桥区,在三十年代,当地曾聚集了多家高档餐厅。——中译者注
[14] 青年印刷经营者联盟的委员长。——原注
[15] 民主商工会(民商)是由日本共产党发起的中小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在全国各地共有615个民主商工会,它们的全国性组织是全国商工团体联合会(全国商工団体連合会/ぜんこくしょうこうだんたいれんごうかい),1951年8月3日成立。——中译者注
[16] 平生釟三郎(平生 釟三郎/ひらお はちさぶろう,1866年7月4日——1945年11月27日),生于美浓国加纳蕃(现为岐阜县岐阜市加纳町),父亲是加纳蕃蕃主的家臣。1881年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1886年入读东京商业学校,1890年以首席毕业于高等商业学校,1893年担任兵库县神户商业学校校长,1894年进入东京海上保险工作。1924年担任大正海上火灾保险会长、扶桑海上火灾保险会长,1933年任川崎造船所社长。1935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1936年担任文部大臣,1939年担任日铁矿业会长,1940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会长、日本制铁社长,1941年担任日铁矿业社长、铁钢管制会会长,1942年任重要产业管制团体协议会会长,1943年任枢密顾问官。1945年去世。——中译者注
[17] 汤泽三千男(湯沢 三千男/ゆざわ みちお,1888年5月20日——1963年2月21日),生于枥木县上都贺郡一个神社宫司家庭,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后,进入内务省工作。1929年担任宫城县知事,1931年担任广岛县知事,1935年担任兵库县知事。1936年担任内务次官,1940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理事长,1942年2月7日——1943年4月20日担任内务大臣。战后被公职追放,追放解除后,担任过中央社会保险医疗协议会会长、市町村建设促进中央审议会会长、明治神宫总代等职务。1959年代表自由民主党竞选参议员成功。——中译者注
[18] 三轮寿壮(三輪 寿壮/みわ じゅそう,1894年12月15日——1956年11月14日),生于福冈县糟屋郡蓆内村(现属古贺市),父亲是村长。192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当了律师,担任过日本劳动总同盟和日本农民协会的法律顾问。1926年担任工农党书记长,同年年底工农党分裂后,担任日本劳农党书记长。1932年参与创立社会大众党。1937年当选众议员。1940年社会大众党解散后,积极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担任大政翼赞会联络部长、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厚生部长。战后加入日本社会党,担任第二东京律师会会长(第二東京弁護士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副会长。1952—1956年当选众议员。1956年因肺癌去世。——中译者注
[19] 菊川忠雄(菊川 忠雄/きくかわ ただお,1901年3月1日——1954年9月26日),生于爱媛县越智郡一个鱼类批发商家庭。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26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作。1936年担任日本劳动同盟本部总干事,1941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中央本部文化部副部长。战后加入日本社会党,担任日本矿山工会(日本鉱山労働組合)会长,1954年在洞爷丸海难中身亡。——中译者注
[20] 日本无产阶级戏剧同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演劇同盟)瓦解后,村山知义于1934年9月鼓吹“新剧团大团结”,成立了新协剧团(新協劇団/しんきょうげきだん)。1940年8月19日,新协剧团遭到镇压,被迫解散,以村山知义为首的26人被捕。战后,村山知义等人于1946年1月19日重建新协剧团,1959年1月15日,新协剧团与中央艺术剧场合并为东京艺术座。——中译者注
[21] 村山知义(村山 知義/むらやま ともよし,1901年1月18日——1977年3月22日),小说家、画家、剧作家生于东京市神田区一个海军军医家庭,1921年考入东京大学哲学科,1922年发表童话画集《罗宾汉》,以新锐画家的身份参加先锋艺术运动。1925年12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芸連盟),并加入美术部。1926年10月创立左翼剧团“前卫座”。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分裂后,于1928年4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全日本無産者芸術連盟)。1929年2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劇場同盟)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5月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31年5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0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連盟)。1932年4月被捕,1933年12月出狱,1934年3月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3年。1934年9月主持创立新协剧团。1940年8月被捕,1942年月获释,1944年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5年。1946年2月重建新协剧团。1960年出任日本演出者协会理事长。1965年参与创立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并担任副议长。——中译者注。
[22] 八田元夫(八田 元夫/はった もとお,1903年11月13日——1976年9月17日),戏剧导演。——中译者注
[23] 候鸟运动(Wandervogel)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兴起的青少年远足运动,纳粹上台后,候鸟运动被纳入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日本也曾引进该运动。——中译者注
[24] 奥多摩(奥多摩/おくたま)是东京都最西北端的町,御岳山(御岳山/みたけさん,海拔929米)和里高尾(裏高尾/うらたかお)都在奥多摩附近。——中译者注
[25] 景信山(景信山/かげのぶやま)位于东京都与神奈川县的边境,海拔727.1米。——中译者注
[26] 原日本印刷工业分会青年部长。——原注
[27] 曾有作品入选日本美术展览会。——原注
日本美术展览会是日本规模最大的综合美术展览会,自1907年起,每年11月在东京举办,展期约为一个月。——中译者注
[28] 战后当过日本共产党东京中央区区议会议员。——原注
[29] “阵场山”现名“阵马山”(陣馬山/じんばさん),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交界,海拔854.8米;小佛岭(小仏峠/こぼとけとうげ)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里高尾町和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交界,海拔548米。——中译者注
[30] 石川达三(石川 達三/いしかわ たつぞう,1905年7月2日——1985年1月31日),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一个英语教师家庭。1927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英文科,1930年前往巴西,数月后归国,1935年利用在巴西的体验创作的小说《苍氓》(蒼氓)荣获第1届芥川龙之介奖。1938年1月,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采访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创作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生きてゐる兵隊),发表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触怒了军方,被判处监禁4个月缓刑3年。战后曾担任日本笔会(日本ペンクラブ)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文艺著作权保护同盟会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31] 《结婚的生态》(結婚の生態)是石川达三的小说,发表于1938年。——中译者注
[32] 那须高原(那須高原/なすこうげん)是枥木县北部的那须岳南侧的山麓地带的统称,白河关(白河の関/しらかわのせき)是著名的关隘。——中译者注
[33] 大菩萨岭(大菩薩峠/だいぼさつとうげ)是位于山梨县甲州市盐山上萩原与北都留郡小菅村鞍部的交界处的山道,海拔1897米。——中译者注
[34] 云取山(雲取山/くもとりやま)位于东京都、埼玉县、山梨县的交界处,海拔2017.13米。——中译者注
[35] 奥武藏(奥武蔵/おくむさし)高原是埼玉县西南部的山岳丘陵地带的统称。——中译者注
[36] 正丸岭(正丸峠/しょうまるとうげ)是位于埼玉县饭能市和秩父郡横濑町交界处的山道,海拔636米。——中译者注
[37] 涉岭(渋峠/しぶとうげ)是群马县吾妻郡中之条郡和长野县下高井郡山之内町之间的山道,最高点海拔2172米。——中译者注
[38] 赤城山(赤城山/あかぎやま)是一座死火山,位于群马县境内,是日本百大名山之一,海拔1827.6米。——中译者注
[39] 日本有两处名为“凤凰山”的旅游景点,一处在山梨县,一处在秋田县,这里讲的应该是前者,其由地藏岳、观音岳、药师岳三座山峰组成,统称“凤凰三山”。——中译者注
[40] 升仙峡(昇仙峡/しょうせんきょう)是位于山梨县甲府盆地北侧的一处溪谷,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游览胜地,号称“日本五大名峡”之一。增富温泉(増冨温泉/ますとみおんせん)位于山梨县与长野县交界处的秩父多摩甲婓国立公园的西侧,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中译者注
[41] 战后当过大日本印刷工会书记。——原注
[42] 《勃朗峰上的暴风雪》(Stürme über dem Mont Blanc)是一部德国电影,由阿诺尔德·范克(Arnold Fanck,1889—1974)编剧和执导,1930年12月25日首映。——中译者注
[43] 在日本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下,大和抚子(大和撫子/やまとなでしこ)是凝聚了传统女性美德的完美女性的代名词。——中译者注
[44] 与山本广次结了婚,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原注
[45] 战后当过安信舍工会妇女部长。——原注
[46] 上文明明是“水野静江”,但这里不知为什么又变成了“水野静枝”,可能是笔误。——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