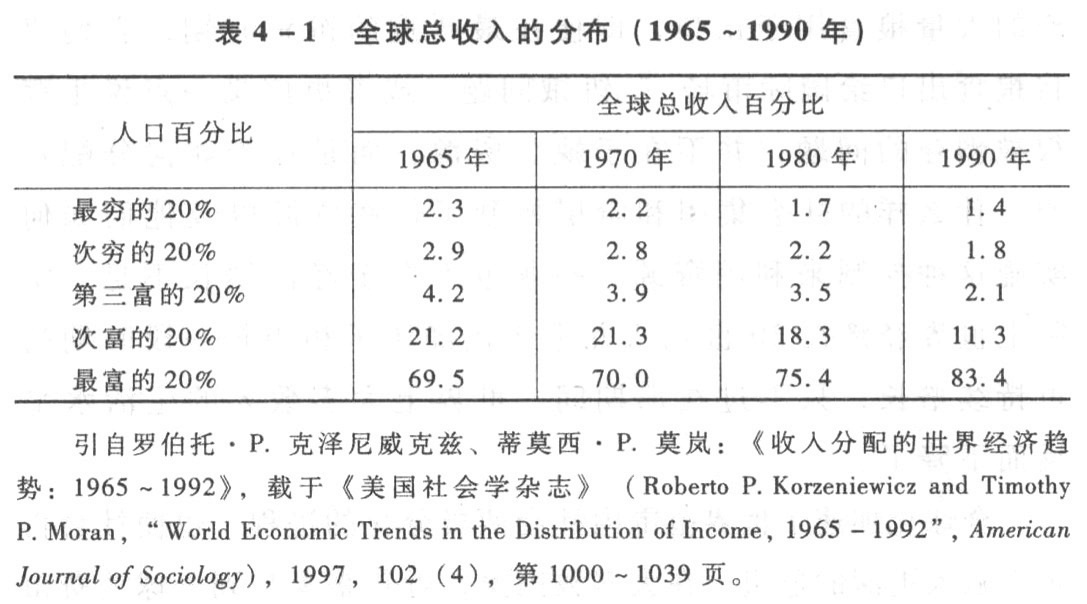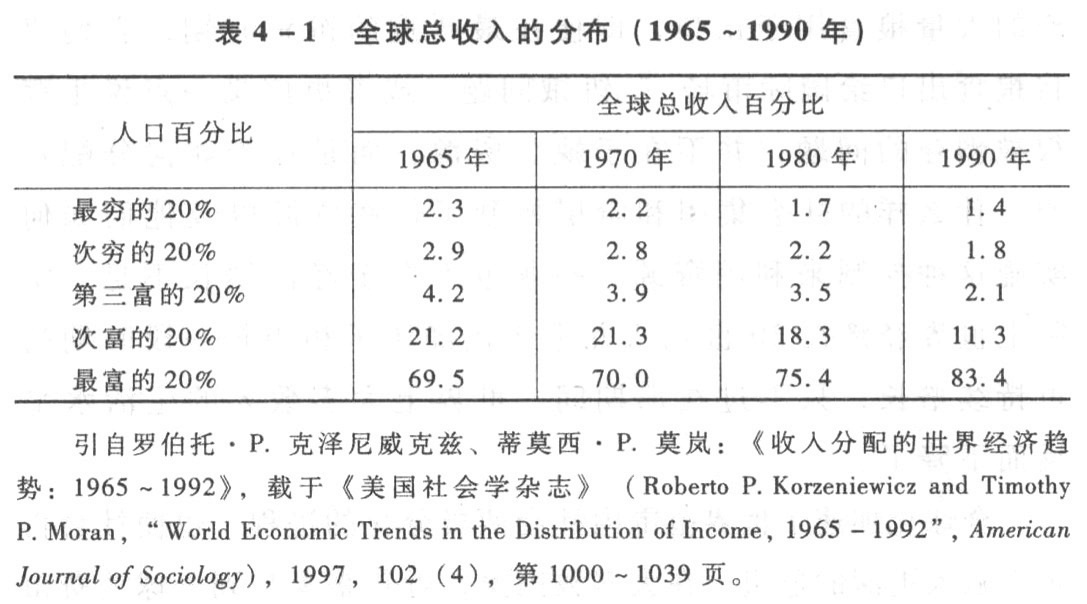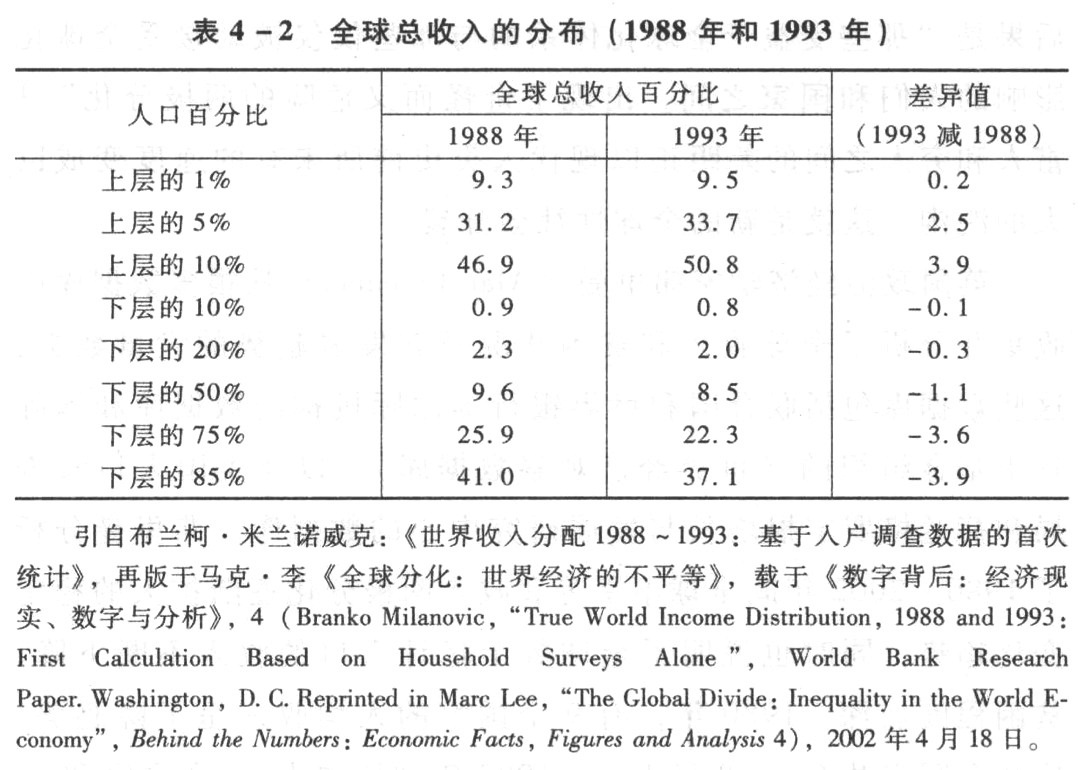全球各种社会力量在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上齐聚一堂。各种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各种运动组织、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伟大的联盟,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不同于当前主流发展模式的全新社会,在当前的主流发展模式中,只有自由市场和金钱能用来衡量财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全球化和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代名词。阿雷格里港论坛则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即我们完全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人类和自然才是我们最最关注的。
我们属于兴起于西雅图的运动。我们向精英阶层及其不民主的做法发起挑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他们不民主的典型表现……
我们这些男人、女人、农民、工人、失业者、专业人员、学生、黑人和原住民,既有来自南半球的,也有来自北半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权利、自由、就业和教育而斗争。我们反对金融霸权、本土文化消亡、知识垄断、大众传媒、通信、自然环境恶化,以及跨国公司和反民主政策对生活质量的严重破坏。类似于阿雷格里港论坛这样的参与式民主使我们认识到,采取另一种具体形式完全是可能的。我们重申,跟金融和投资需求比起来,人类、生态和社会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
[46] 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恶化,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组织的几万人走到了一起,参加此次阿雷格里港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尽管有人试图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仍然齐聚于此。我们再次走到一起,为的是将我们反对战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为的是强化我们在上届论坛上达成的共识并重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当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既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城市的,既有在职工人也有失业人员,还有原住民、无家可归的人、老年人、学生、移民、专业人员,大家也都分别属于信仰、肤色和性别观念各不相同的民族。表现出这种多元性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联合的基础。我们是全球性的联合运动,我们一致反对財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困和不平等的扩大化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因为共同的决心和信
念而走到了一起。我们正试图构建另一种体系,并且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共同的斗争和反抗,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联盟,共同来反对一个建立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崇尚暴力基础上的体系,这一体系代表了凌驾于民众需求和期望之上的资本利益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每天都在上演着女人、孩子和老人濒临死亡的惨剧,他们都死于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或本可预防的疾病。很多家庭都被迫背井离乡,这都是因为战争、“大发展”的冲击、失去土地、自然灾害、失业、对公共服务的打压、社会凝聚力的消失。不管是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各种为了维护尊严的斗争和抵抗都正在风起云涌。
[47] 在全球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聚集在阿雷格里港召开此次会议。美国的好战倾向导致它决定向伊拉克发动战争,这对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生动地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看到了黩武主义与经济统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身也处于危机当中:全球都在呈衰退趋势,这一威胁已然存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贪污丑闻,这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和
经济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权利和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社会运动反对的是黩武主义、军事扩张和国家镇压,国家的武力镇压产生了无数难民,穷人及其参与的社会运动都被扣上了犯罪的帽子。战争已经成了全球霸权结构的一部分,全球霸权习惯于使用武力来控制民众和石油之类的战略资源。美国政府及其盟国越来越把战争当作解决冲突的常用方案……
上述所有这一切都威胁着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坚决反对!
[48]